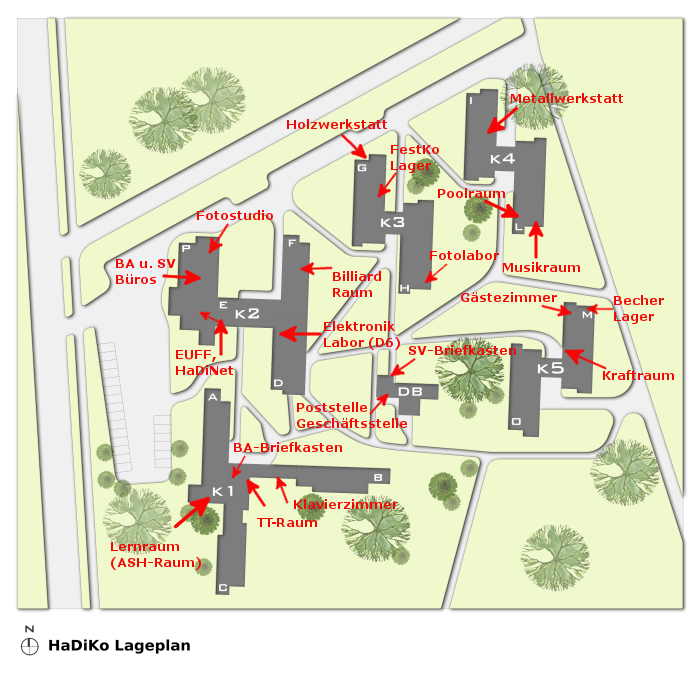卡鲁城里有个围棋俱乐部。棋客每周二聚集在一个酒馆里下棋喝酒聊天。这样的业余爱好团体在一个城市里有很多。一个人若没有参加过业余爱好俱乐部,在旁人眼里是无趣的。
W同学和Z同学精力有余,加上日益增长的围棋兴趣,参加了这个俱乐部。在一个30万人的欧洲小城,居然有一二十人的对这一古老的中国棋艺着迷,这也是匪夷所思的。
我去过没几次。因为那时学习压力很大。我当时必须阅读大量专业书籍,寻找一个上得了台面的研究课题,并取得新的进展,从而写出博士论文。
那时,中日围棋擂台赛正酣。卡鲁围棋俱乐部有人提出,咱也来个中德围棋擂台赛吧。中方已有五个棋手,德方也出五棋手。倡议一经提出,无人能抵抗,这倡议诱惑力太大了。
于是乎,双方各自布阵,调兵遣将。每周二就在这个小酒馆杀将起来。那时节,Z同学还没进厕所研究棋谱,所以我被推为卡鲁的聂卫平,Z同学为保卫擂主的阵前大将。经过多个回合,双方只剩下各自的擂主与Z同学。德方擂主老R身材魁梧,脸相却斯文,一副银丝眼睛,还是个物理博士。Z同学上场搏杀,虽竭尽全力,然功力不敌,败下阵来。
轮到双方擂主对决了。这场对决吸引了全体棋迷。因为输赢并不好说。事先双方各有输赢,棋力相差不大,决战因而精彩。
需要埋个伏笔的是,欧方真正的实力在于一位卢森堡籍的青年小L,棋力当时就高达四段,欧洲业余冠军。这位后生实力实在太强大了,被中方生生排除,理由是,咱们是中德擂台赛,卢森堡人不能算吧。
擂台赛的擂主经过激战,老R获胜。也就是说德方赢了。老R非常高兴。散伙时,老R坚持要用他崭新的奥迪送我回家,抚慰我失败的沮丧?我怀着失落与感激坐进他的奥迪新车。天下着瓢泼大雨,雨刷也来不及刮去倾盆而下的大水。在一个十字路口红灯停下,老R轻松地说着段子。绿灯一亮,老R左拐。我忽然看到一辆汽车出现在眼前不远,老R来不及躲闪了,轰的一声,撞上了。在关键的时候,看出德国人的老练了。老R马上问我,受伤了吗?我摸了摸头上与身上,说,还好没有伤。老R在车里座椅下黢黑的摸半天,摸到两副眼镜,一副是他的,另一副是我的。他递给我一副,说,我们下车吧。打开车门,撞车双方并不多话,打电话叫警察。警车几分钟就赶到了。询问了几句老生常谈的问题,红绿灯状况,系安全带没有,等等。警察问完情况,核实证件,双方签字后,警车就走了。双方的车全都毁了,等待拖车拉走。老R与对方开了个玩笑说,恭喜你可以换新车了。对方耸耸肩。忽然老R直直看我半天,怀疑他眼睛是否撞出毛病了,因为他看不清楚我。我说,我也怀疑是否眼睛出了毛病,我怎么也看不清你了呢?忽然,老R摘下眼镜递给我说,这是你的眼镜。我恍然大悟,摘下眼镜递还给老R。
这场擂台赛当然也吸引了中国学生会,大家正等着好消息。正当我们要沮丧地宣布败绩的时候。一架飞机从上海飞来。下来一位围棋仙女,中国国家队芮九段的师妹小Z。我方马上派出Z同学,与德方商议,双方各增补一名队员,把中德擂台赛升级为中欧擂台赛。德方很大度,宣布接受,擂台赛继续,丝毫不计较老R已经为擂台赛付出了一辆新奥迪的代价。
小Z没顾上倒时差,赶赴擂台。中欧双方所有棋手对这场邂逅充满兴趣。小Z没下几手就给了老R压力。老R脸色凝重,知道大事不妙了。又过了一周,小Z与小L对决,这是卡鲁有史以来最高水平的一场围棋赛。双方的棋力都在四段以上。不管是专业段还是业余段,卡鲁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高水平的围棋赛。开创了历史!这场围棋擂台赛,这段留学往事恐怕在欧洲也是空前的。因为小L是欧洲冠军呢!比赛结果,Z小师妹力克群雄,成为唯一不败的中国围棋手,赢得了这场擂台赛。实际上,是德方赢得了中德擂台赛,中方赢得了中欧擂台赛。
这场擂台赛的一个文化影响是,以上提到简称名字的欧洲棋手后来都成了中国女婿。Z小师妹后来成为中欧围棋大使。
封面图片源自 Quelle: flickr.com